《不认输,你就不会输》在线阅读试读|段诗闻
重于鸿毛,轻于泰山
我被朋友叫去给遭遇车祸
而被迫截肢的紫研做心理辅导,
结果却被她所辅导、拯救。
夜里的意外
“今天我们去哪呀?”
当我们的SUV驶出医院的地下停车场,第一缕刺眼的光线穿过我的发梢射入眼睛的时候,坐在驾驶座位上的小艾这么问道。
“去海边!”
坐在后座上,全身被各种束缚带五花大绑起来的紫研大声说道。这一声呐喊仿佛用尽了她身体的全部力量,喊完后她就大口地喘起粗气,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她也跟着笑,整个车厢里弥漫着一股类似于椰子果肉般的清香的笑意,让人欢快。
“哇呜!”
在我们的欢呼声的伴奏下,车子掠过小巷,掠过两旁低矮的白色房屋。那些房舍楼顶下栽种着绿色的植物,看上去就像是夏天我们爱吃的香草冰激凌;在我们还在回味着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的时候,车子已经掠过市中心的商业区,宽阔的马路旁林立的高楼玻璃幕墙上显示出天空的倒影,使得那些楼宇看上去就像是明朝的精美花瓶;接着,车子掠过跨海大桥,桥面两边的护栏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银光,那远处的海岛从车窗看过去,就好似立在护栏上的标识牌,提示着我们海滩已经不远。
这是个久违的晴天,连续一周的雨,把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都洗刷得干干净净。初夏的雨就像是一位魔法师,他大手一挥,指力所到之处,所有的一切都焕然一新,变得像是才从蛋壳里探出脑袋的小鸭子一般可爱。
这SUV的主人就是坐在后座被束缚带绑着的紫研,紫研个子很高,尤其是那双腿,更是生得修长。她坐在后座,虽然SUV的空间还算宽大,但是她的腿还是得蜷曲着,大家都担心她会不舒服。但是她却笑着让大家放心:“没事,你们知道的,我这腿上也没有知觉。”这辆车本来是要在紫研入院之后就被拖去拍卖的,后来经过紫研的央求,她的妈妈才答应帮她留下来。现在,车子被紫研授权给朋友小艾使用,条件是小艾每个周末都得载着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出去兜风,紫研说这是“传统”,不管她在不在医院里都不能被破坏;紫研最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玩,她每个周末都会载着他们一起去海滩散心。当初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她才找了妈妈借了点钱,自己贷款买了这台SUV。
紫研今年大四,原本在一家做期货生意的金融公司实习,深得同事和管理层的喜爱,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很优秀。男朋友比她大五岁,在一家IT公司任产品经理。据紫研的妈妈回忆,两人感情很好,平时也很合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是一场车祸搅乱了她的生活。那天,紫研照例在公司加班。整个小组的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位上赶报告。忽然,一位同事借故离开,没过多久便捧着一个蛋糕走回办公室,对着大家宣布说这是一个惊喜。因为他们组的一位同事今天过生日。紫研当然要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在吃蛋糕的时候,她一时高兴喝了一点酒精饮料,当时,她还因为这个跟同事们开玩笑说,希望今晚早点下班,因为她不能开车了,如果赶不上最后一班巴士,又打不着出租车的话,她就回不了家了。
很凑巧的是,或者说很不凑巧的是,当紫研下班去赶最后一班巴士,正走到离车站不远的一个路口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恰巧从她身边驶过。她拔腿便追了上去,因为经常练习跑步的缘故,她身体的爆发力与耐力都很好,所以,很快就追了上去。她的举动也引起了巴士司机的注意,于是巴士司机停下了公交车,在车站等着她跑过来。可就在她沿着人行横道穿越马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辆由一个醉酒的年轻男子开着的保时捷,以超快的速度闯过了红灯,就像一颗命中目标的导弹一样,兴奋地撞在了紫研的身上。随着剧烈的刹车声,紫研腾空而起,就像是一颗从高处坠落而触地反弹的篮球那样,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曲线,然后动能损耗殆尽,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那之后的事情,我便没有过问了。在那次意外的五个月之后,我被叫到了她的身边,那时候她已经被确认为是低位截瘫。
低位截瘫
我是这么被叫来的。
一个阴沉沉的春天的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位在社区残障者服务机构工作的朋友打来的,我一接起电话,他就在那头像是扣动了冲锋枪扳机似的说道:“我给你找了一个活,服务对象是一个女孩,大概22岁,五个月前遭遇了一场车祸,导致了低位截瘫,有通过康复训练恢复的可能,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上去,康复训练没什么作用。”
“等等,具体点,你让我做什么?”我不得不打断他。
“像往常一样,协助我们进行心理干预。”他笑了起来,“你不是挺喜欢干这样的活吗?”
“可是我现在要上学啊。”
“少废话,滚过来,往返路费、食宿费我报销。”在我就要放下电话的时候,他又换了种口气补充了一句,“保证你不会后悔!”他故意沉下了嗓音,甚至还带着些许鼻音,慢慢地吐出了这些字眼,就像老式的蒸汽机车,在到达终点站之后,慢慢地排出沸水炉里的气体那样,我似乎可以看见那红色的车轮下面冒出阵阵白烟的场景。
之后,我便开始了每两周一次的飞行之旅,往返于南部沿海和神州腹地之间。
第一次见到紫研,是在她所住医院的康复科。当我从机场乘坐出租车赶到医院楼下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住院部的楼道间已经弥漫饭菜的香味了,那些戴着白帽子的工作人员,推着一辆辆盖着盖子的装满菜饭的车子站在电梯前排队,等着把这些“报时器”送到各个楼层,提示人们中午的到来。我跟着一位推着车子的阿姨挤进了电梯,电梯里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那股油腻的肉香一块涌入我的脑海,那种感觉就像站在某人的呕吐物旁一样,这让我想起了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病患。
他当时二十岁出头,因为车祸被截了肢,双下肢膝盖以下的部位都被锯了去,腿的末端再也不是那个有五个指头的爪子,而是一个光秃秃的蘑菇,而且白痴痴的,就像白色蜡烛的残骸,好不吓人。
他焦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发脾气就用手抄起床边的板凳向门口扔,有时会砸在门板上,留下“铛”的一声。他甚至都不能看见自己截肢的部位,如果不小心看到了,他就会感到反胃,甚至直接吐出来。有一回,我和他聊天,聊着聊着他就不可抑制地去扒开裤腿看那动过手术的地方,看了一会儿,他就忍不住趴在床边吐了起来,呕吐物如同发酵不彻底的酒糟和了水,一段段地从他嘴里流出来,让我也跟着反起胃来。吐完之后,他哭了,嘴里念叨着:“截了肢,我这以后怎么办啊?”而我就站在一旁,无力安慰他。
这个时候的人们最不缺的就是安慰,那份苦痛并没有办法被安慰。史铁生这样描述他瘫痪初期时的情景:双腿瘫痪以后,我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这时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圈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瘫痪以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
这样的苦痛来自于我们的求生本能,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或战或逃的冲动,而无论是战斗或者是逃跑,都需要我们身体的响应,而瘫痪不仅使得我们的身体无法反抗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的潜在危机,它本身就是一种危机,而瘫痪的事实又不是能够通过我们的个人努力而改变的,这就等同于让我们时刻暴露在危险之中,就好比有一头狮子张着血盆大口,整天在我们周围转悠,我们却无法逃开。
而且,丧失了自由行动的能力本来就会给人一种很大的无力感,就像是你倒在一口井前面,虽然嘴里面很渴,却无法移动身体接近那水源一样。再加上我们的社会环境,很多工作是一个瘫痪者无法完成的,这会使得瘫痪者对自己未来的生计产生担忧,又加之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历来就不完善,那种担忧就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的恐惧。
当这些情绪被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就化作了一种戾气,这种戾气需要发泄。社会上的不平等也会产生一些戾气,那戾气的发泄口可能是一壶在火锅店里泼向食客头上的开水;也可能是点燃浇在汽车上的汽油的那一把火。对于瘫痪者来说,这股戾气的出口就是那已经失去功能的器官。他们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这个部位上,把全部错误都怪罪到这个器官上,他们会击打、咒骂那个身体部位,有些人甚至会自残,好像伤害自己的肉体可以减轻心灵上的疼痛似的。
这些行为都很正常,至少是可以被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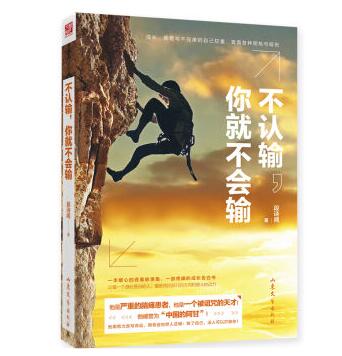
在我小的时候,我也曾经绝望过。我坐在床上,靠在由被子架起来的垫子上,我的左手边是一扇窗户,抬起胳膊,指尖就可以触碰到玻璃,那玻璃凉凉的,玻璃的外面是炙热的阳光和玩耍的孩子们,那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鲜艳得就如同夏天盛开的鲜花,他们帽子上的圆点就是那躺在花心的黄色花蕊,迎着风在摇动。他们好像在玩着捉迷藏,那个古老的游戏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男孩女孩们在楼下的空地上跑着跳着,利用电线杆和楼梯洞的拐角掩饰着自己,祈祷着同伴不要捉住自己。然而,不管有没有被抓住,被抓住的和没有被抓住的都很开心,笑着叫着。我也渴望着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我不行,因为我不会走路。
我无数次地责问命运女神,为什么要将这种不幸降临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要用一层透明的隔膜将我隔离在窗户里面?窗外有欢声笑语,可是我够不着,摸不到。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心里就越是想要,我也想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于是我开始怨恨自己,怨恨我的小脑,怨恨我的双腿。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都不可以听见“脑瘫”这个词,一听到有人谈论这个,我心里就翻江倒海,那种痛苦就像是有一把锯在我心里来回地切割着,我能听见那利刃发出的声音。那是我生命里的冬天,寒冷而又干旱的冬天,因为缺乏雨水的滋润,我的世界渐渐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变得灰蒙蒙的。
所以,我想每个人瘫痪之后,他的世界都会变成灰色吧!
也许这就是我的那位朋友把我叫到紫研身边的目的吧!大概也就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吸尘器,把她世界的污垢都除去,还它一个彩色的景致吧!怀着这样的想法,我走出了电梯,来到了紫研的病房门前。房间的门虚掩着,从门缝中飘出一种茉莉花的香气,走到近前就好像置身于初夏时节的山谷前,那谷中开满了鲜花,到处飞舞着如同小精灵般的蜻蜓和蝴蝶,偶尔从峡谷的另一边吹来一阵风,那满谷的花香便扑面而来。
我敲了敲门,一个清脆的女声答应我,如同悬挂于门廊的风铃,欢迎着我的到来:“请进。”
“你也出过车祸?”她看见我走路的样子,笑着和我说,“那一定很有趣。”
“没有,”我向他解释道,“不过,那也是个意外,是在我出生的时候发生的一次医疗事故。”
“哦,原来你从一出生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呀。”说完,她就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边笑着边把摊在被子上的书合上,在她将书放到床头柜上的时候,我瞟了一眼书的封面,看到了两个大大的字——云南,那是Lonely Planet的路书。
这时,站在紫研旁边的一位男士看了看手机,然后,抬起头对她说:“我该走了,明天咱们沙滩上见。”说完,便弯下身子抱了抱她。接着,他转过身来,对着我笑了笑,打了声招呼,便拉开门离开了。
“我前男友。”紫研看着那离开的背影跟我解释道,“我们上星期刚刚分手。”我想他们的分手也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吧,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
两个巫师
初次见面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这家人的一个大仪式——请巫师来为紫研作法。这是紫研母亲的决定。紫研的妈妈是个政府部门的小领导,其实并不迷信,也不笃信任何宗教。用紫研的话说,她的母亲之所以会请来萨满法师前来作法,完全是一种将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投机心理。说这句话的时候,紫研的妈妈就在旁边,所以,紫研还特意把我拽到她的身旁,让我贴近她的嘴巴,故意压低声音对我说:“我,就是那匹死马。”说完,抿着嘴忍住笑意,移动眼球瞟了瞟她的母亲。
那个巫师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那道袍的帽子也遮不住她灰白的头发,它们从帽子的边缘渗了出来,看上去就像是没有烧尽的纸钱的灰烬。
她念着咒语,摇着铃铛,在屋子里面转了几个圈,然后,点燃了她手中的几道符,就算是做完了整个仪式。她点燃手中黄色纸符的时候,我嫌烟气太重,又怕咳嗽声打断了她的施法,便拉开门躲了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紫研妈妈的眼睛红着,里面有一些稀薄的液体在打着转。紫研的护士这时候也在门口站着,她冲我笑笑,我不好意思地跟她解释道:“里面烟气太重,出来透透气。”她被我尴尬的样子逗笑了,笑着摇了摇头:“没事,病急乱投医而已,只要病人的亲属开心,医院对这种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任何一个母亲遇到自己的女儿出车祸,估计都会着急上火吧。我的母亲就说过,哪怕要她倾家荡产,她也会把我的疾病治好。从紫研母亲红着的眼睛里看得出来,她比我妈妈的内心还要急切。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站起来,就那么永远瘫痪在床,那么他的人生又该多么凄凉,想到这个,任何人都会毛骨悚然。是的,毛骨悚然。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我拿到了紫研的档案,更加理解了为什么紫研的母亲会如此着急。
紫研曾经特别爱好长跑,她几乎每天都要去跑步,有时候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上十几公里,有时候沿着环岛路跑上一段。我看过一段她描述跑步的文字,她写道:“跑步,是世界上最惬意的运动,跑步令你身心愉悦,当你的身体随着你的脚步一起一伏,你的心跳就变成了美丽的音符。在环岛路上跑步的时候,海风吹着你微湿的额头,一种跟自然一同呼吸的喜悦就像一滴墨水似的在你的心间弥散开来,那是上帝的福音。”
她还特别喜欢旅行,她已经靠着假期兼职穷游了十六个国家,她有个博客专门记录她的行程和感悟。我特意去看了她的所有文章,里面每一篇游记都不仅有记述,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堪称佳作。在她最近的一篇日志中,她这么写道:“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故,不过我会找出继续旅行的方法的,我很期待再次和大家在这儿见面。By the way,我的下个目的地依然是云南。”
在她的档案里,我还看到了她刚从车祸中苏醒过来后的记录。那上面说:在她刚刚发现自己的下肢没有知觉的时候,志愿者曾经试图安慰过她;但是她和志愿者说,她之前看过很多描写某人瘫痪之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史铁生的一些作品,那上面所谓的苦难她觉得大多是作者自己的想象,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她不会太难过。
那份记录的后面,有一位心理辅导员的评估报告。那上面说,此病患有一些防御心理,需要有一个人来突破她的心防。我看了之后,不禁在心里笑起来。这大概就是我被叫到这儿来的原因,可是不能因为人家面对我们大家都认为是一种“灾难”的事不难过,就断定她一定没有敞开心扉。不过,她能那么说也让我吃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倒像是一个巫师。
重要的是选择
跟紫研在一起很轻松,我们俩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所以有很多话可以说。像紫研一样,我也很喜欢长跑和旅行。所不同的是,她在国内的旅行基本上都是搭车,而我基本上都是坐火车。她经常和我说起搭车旅行的快乐和惊险,而我则和她说起火车飞跃黑夜、飞过田野、划过湖泊时的心情。经常一下午的时间,就在这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度过了。而到了我写评估报告的时候,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次即使交不出报告,我的朋友既没责怪也不催促。
年轻人的聊天自然逃不开感情问题。有一天,我这么对紫研说:“关于男朋友的事情,也不要介怀,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发生这样的意外之后被分手,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料,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她就笑了起来:她笑起来的样子真美,就像是猎户座里面的一颗小星星。“你怎么知道我是被分手的?”她笑够了,正色道,“是我跟他提出的分手。”
“想说说细节吗?”
“嗯,有点不好意思。既然开头了,我就说吧。你知道的,虽然是低位截瘫,但是我从骨盆以下的部位还真就是没有知觉,即使是做爱,我也没有感觉。在我瘫痪之后,我们做过两次,但不仅仅是下面没有感觉,事实上当他亲吻我和抚摸我的时候,感觉都不一样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人们常说的肉体和灵魂是一体的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当我没有了那些感觉的时候,我看待感情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想,我可以重新做出一些选择,于是我就和他分手了。”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其实,我知道他也想跟我分手,但我知道先开口对他很难,因为他身边的朋友、社会舆论还有他自己的道德意识都会谴责他,所以应该由我来说。人们常常说,在恋人遇到变故的时候抛弃恋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比如说当恋人瘫痪的时候。瘫痪当然没有那么轻松,但也没那么沉重;就像是爱情,爱情当然不应该那么轻,轻到没有什么重量,但也不应该那么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她停下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接着说,“就像是你,我看过你的心理干预报告。其实,除了橘子,你根本就没遇到过让你着迷的女孩子,但是你偏要说自己喜欢她们。只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无论你怎样辩解,别人都不会以为是你没遇上自己喜欢的人,而是会认为没人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你只是害怕失败,你只是害怕会成为别人口中的失败者。”
“渣男,我就是个渣男。”我说。
“也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是你把成败看得太重了而已。”她倒是很轻松地说。
可是我奇怪起来:“你从哪看到的那些报告。”
“你朋友给我的呀。”就是那个打电话叫我来的家伙。
最后一次见到紫研已经是秋季,那时我已经进行了半年的来回飞行,这是我最愉快的一次心理干预行动,其实与其说紫研是我的服务对象,倒不如说我是她的服务对象。最后一天下午,我来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收拾行李,她告诉我,她要乘坐晚上八点的飞机去昆明。
她终于要去云南旅行了。
她摇着轮椅,在家里四处进进出出,就像是一只刚学会走路的小兔子,又像是第一次要出远门的小孩子,脸上透出一种成熟苹果的光芒。我问她要不要搭把手,她笑着说都是女生的衣服,等会帮她拖箱子就行。在她拉上登山包的拉链的时候,她这么跟我说:“很可惜,这一次不可以搭车了,幸好我还可以旅行,人总是得变一变的,不是吗?哦,你能帮我叫辆出租车吗?”
站在机场值机柜台前面,看着紫研坐着轮椅忙碌的身影,我突然感到欣慰。我想,瘫痪也没有那么严重。同样的,我的脑瘫也没有那么严重吧?我们常听到,某某重于泰山,某某轻于鸿毛。那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事实上并没有那样的事情,大多数事情都没有那么沉重,当然也没有那么轻巧。如果说瘫痪是人类的一种苦难,我想那种痛苦并不是瘫痪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的头脑对于瘫痪这个事实的判断和抗拒所带来的。换句话说,是我们选择了痛苦。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痛苦与沉重,我们当然也可以选择愉快与轻松。
那个把我叫到紫研身边的朋友这时候带着我的登机牌来到了我的身边,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了吧?她是个巫师,不是吗?拿上登机牌,回家吧,我以后不会再叫你做这些事情了,都结束了。”是,一切都结束了,我与脑瘫的战争也结束了。这一切虽然不轻松,但也没那么沉重。